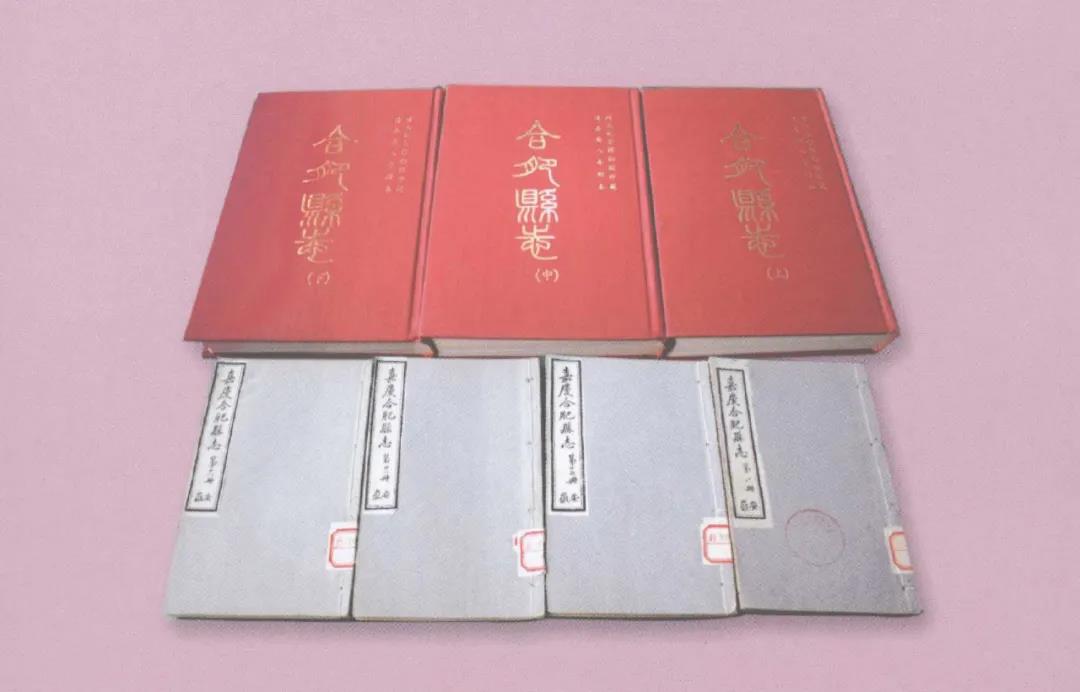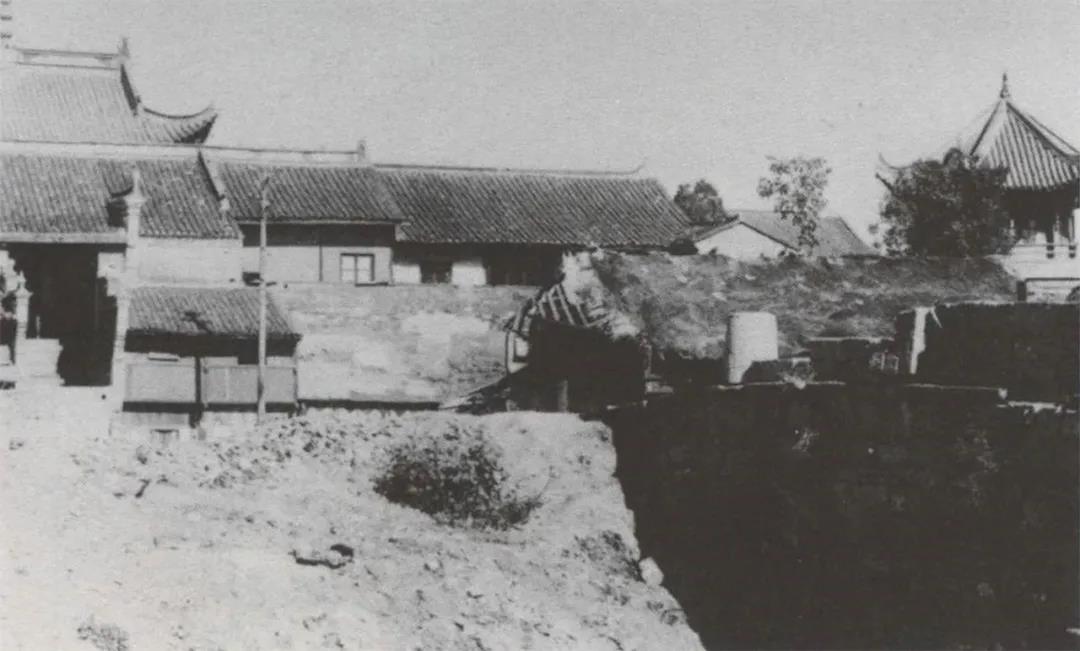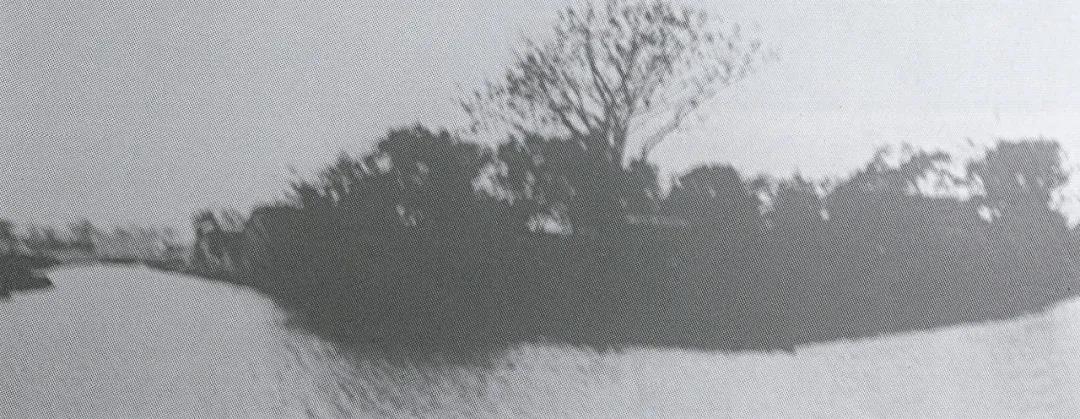編者按國有史,地有志,家有譜。方志綿延編修千年,全面并系統地記述地方的自然、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社會的歷史與現狀,成為了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大瑰寶。了解一座城,當地方志特別是古舊版本值得深入閱覽和解讀,除了豐富的知識信息,其中不乏趣味性和新奇的事物。這一期,讓我們了解一下合肥動物故事。
合肥曾經“虎出沒”
看到小標題,有讀者笑了,哪要“曾經”呀?現在大蜀山腳下的野生動物園內,老虎的聲音還在此起彼伏呢。咱們今天說的,可不是關在籠子里、整天苦惱的“大貓”,而是活生生、一掌致命的野生虎!
圖|東北虎@合肥野生動物園
據嘉慶《合肥縣志·祥異志》記載,“(清康熙)五十四年六月,大蜀山有虎至,白天傷人。”康熙五十四年,即1715年,距今三百多年。三年后,“五十七年(1718)閏八月,(合肥)南城外有虎至,連爪死一人、傷二人;東鄉包城灣又爪死一婦人。”一百多年后,同治元年(1862)春,六十多公里外的廬江縣爆發“饑、疫”,“豺虎入市,噬人”。
圖|大蜀山攝影@淝南居士
從大蜀山到“南城外”、“東鄉包城灣”以及廬江的“市”,老虎已不只是維護自己的棲息地,而逐漸闖入人類社會,進行多次騷擾,甚至是覓食。
圖|虎來源@北京動物園
飛蝗北來民不聊生
老虎的出現是短暫的,在歷代“祥異”記錄中,“蝗蝻”的身影似乎更加頻繁。“蝗”即蝗蟲,也就是大家俗稱的“螞蚱”、“蚱蜢”或者“草蜢”,而“蝻”則指的是它的幼蟲。老虎攻擊人類,而蝗蟲則喜歡人們賴以生存的稻谷,歷代蝗災屢有發生,百姓苦不堪言。
圖|來源@糧農組織/SvenTorfinn
府縣方志對蝗災多有記載,光緒《廬州府志》記有37次,嘉慶《合肥縣志》記有11次,光緒《廬江縣志》記有17次,道光《巢縣志》記有7次。又《合肥市志》引史料稱,唐代以后蝗災達26次之多。目前已知最早的記載,發生在東晉太興二年(319)五月,“淮南、廬江諸郡,蝗食秋麥”。
圖|來源@美聯社/BENCURTIS
蝗災盛行之時,飛蝗自北而來“食稻過半”,致使田間“禾稼盡枯”,“野無遺草”,“民眾饑荒”,隨處可見“餓死之人”,蝗蟲數量多至“塞路”,“遍地皆蝻,人不得行”,有時還伴隨瘟疫并發。其影響范圍,少則一兩縣,多至幾省、數州。解放后,蝗蟲逐漸被消滅。除了蝗蟲,合肥地區還有螟蟲、稻薊馬、稻葉蟬、稻苞蟲、粘蟲、麥蚜、麥圓蜘蛛等谷物害蟲。
圖|來源@糧農組織/IsakAmin
奇異動物層出不窮
前不久,合肥政務區發現一只戴勝鳥,引發媒體爭相報道。其實,古人在對珍貴動物的出現,特別是具有美好意義的物種,也會進行記述,錄入方志之中。以嘉慶《廬州府志》和《合肥縣志》為例,就有白鹿、白雀、白燕、白兔、白鼠、白鴉、赤鳥,等等。
圖|白鹿倉攝影@淝南居士
還有一些比較“特別”的動物和奇異現象。西漢,“元封五年(前106),廬江(郡)獲龜二十枚,長尺有二寸,輸太卜官”。東晉,“(大興)四年(321),廬江縣民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,掘之,得一母犬,青氂(牦)色,狀甚羸(瘦),走入草中不知所在,視其處有二犬子,一雄一雌”。唐代,“(永泰八年,772年),合肥棠梨樹上烏鵲同巢”。北宋,“大中祥符二年(1009)八月,有青蛇出無為軍廨(署),長數丈”。清代,“(康熙)三十四年(1695)七月,合肥縣城內衛山樗樹(即臭椿)上產一鳩,二首、二喙、二目。后大旱”;“咸豐四年(1854)六月,無為鞍子巷胡姓家雄雞生卵,約長寸許,形如人指”;光緒六年(1880),“(巢縣)夏閣鎮南五里村得一鱉,約重六斤,高四寸許,背有覆釜形,鄉人剖其背,中有小兒,形長二寸,生動宛然,踰(逾)時漸縮漸小,化水而沒”。
圖|白鷺戲水攝影@張凌云
當然,還包括了神話動物。北宋,“宣和三年(1121)五月,梁縣民邢喜家,牛生麒麟”。明代,“洪武三十二年(1399)四月,舒城秦鳳家產雞雛,長頸方嘴高足,毛羽五彩,遍身如丹砂,一時傳以為鳳”。又據“舊志云”,清代,康熙三十二年(1693),“麒麟產于(合肥縣)三河鎮民家”,對此嘉慶志據“不著為何物所生,鄭達所記又無”,作出了“此異似不足信”的結論。
圖|小雛雞攝影@張凌云
由于年代久遠,文字記述比較粗略,部分或許可以用變異、畸形等進行解釋,然而絕大多數現象的形成原因已不得而知。今天讀來,“奇怪的知識”增加了,舊方志的趣味性也得到了無限伸展。
合肥動物地名
當然,合肥也有不少動物元素的地名,這里有必要對其作一些介紹。
圖|古九獅橋來源@資料圖片
明代,合肥城有白鶴(左一廂)、車馬(左二廂)二巷,“白鶴巷”即后來的白鶴觀巷(今逍遙津路),“車馬巷”已無考。清代,東門大街北有“蝴蝶巷”(舊云有兩巷,誤)、“白鶴觀巷”,明教寺街南有“九獅橋”,縣橋大街東有“鳳凰橋巷”(通鼓樓巷),德勝門大街,北為“回龍橋”,街東有“回龍巷”(今回龍橋路)。
圖|白鶴觀巷攝影@淝南居士
后來陸續出現的還有,后大街南“龍門巷”,東大街“北馬道巷”、“南馬道巷”,北大街“東馬道巷”、“西馬道巷”,德勝街東“小馬場巷”,等等。一些小巷的俗稱或別名亦與動物相關,比如懷德巷俗稱“殺豬巷”,小史巷又名“小豕巷”等。又,威武門城樓名曰“五鳳樓”。在這其中,馬、龍、豬占比較大。中華民族的傳統圖騰“龍”不用多說,馬是古代重要的交通運輸工具,在軍事中亦發揮著重要作用,而豬則是人們的主要食物來源之一。
圖|小香豬來源@上海動物園
說到動物地名,城郊鄉鎮不可或缺。首先來說一說兩個“金牛鎮(鄉)”。相傳,從前大蜀山中藏有寶物,開山鑰匙埋在城內三孝口紅石的底下,有人聽聞想要盜取。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,盜寶人費了九牛二虎之力,將紅石撬開,順利拿到了鑰匙,然后匆匆趕到大蜀山,將鑰匙放在山上。剎那間,山中一聲巨響,山門緩緩打開,萬道霞光從山洞中向外噴射來,跑出來兩條金光燦燦的牯牛,“哞哞”叫喚。盜寶人急忙要逮,兩條牛受到驚嚇,分別跑向西南深山和東南巢湖,不見了蹤影。又一聲巨響后,山門關閉,匆忙之中盜寶人將鑰匙遺留在山洞中,從此再無第二人打開山門。后來,人們在山南館北和三河鎮南看到過金牛的身影,兩地各以“金牛”命名,即今肥西縣山南鎮金牛社區(曾設金牛鄉)和廬江縣金牛鎮。肥西金牛還有一說,古早時曾有一頭金牛在此破土而出。
圖|耕牛攝影@張恣寬
肥西金牛向東二十多公里,還有一個“防虎鄉”。這里地處紫蓬山南麓,境內有座防虎山,相傳曾有個兄弟倆常身披虎皮,假裝老虎在此攔路搶劫,行人每次途徑都要小心提防,久之延為地名,即今肥西縣柿樹崗鄉防虎社區。古人云“左青龍、右白虎”,肥西防虎已上線,接著便是肥東的青龍、白龍了。
圖|防虎街道來源@微美肥西
肥東縣白龍鎮,相傳曾是古代官辦牧馬場。馬群之中,曾有一匹良馬——“白龍駒”,在其死后,主人不忍心剝食,便連皮埋葬在這里,此后世人皆稱這里為白龍廠(場)。青龍廠社區,相傳清代咸豐年間(1851—1861),張、管兩家在此開設飯店,時稱“張管店”。后來,南京馬治臺為避禍逃至褚圩,被褚老開(褚開泰)收留,馬治臺復職后,褚老開依附馬治臺,在張管店開設了牙行、煙葉、米行,并建造了南、東、北三個營寨,分兵把守。某日,烏云密布,天邊升起龍旋風,寨中有人大呼:“不好啦,龍來了!”從此以后,人們為祭龍,改張管店名為青龍廠。明代,兩地均列入合肥縣二十一所馬廠(場),時亦有黑龍、龍岡、龍安、龍勝等廠。
圖|青龍廠褚老圩舊址來源@資料圖片
關于合肥境內“龍”的地名,筆者在《合肥有座古“龍城”,深藏肥東無人知!》一文中曾有詳細闡述。
圖|龍城遺址攝影@淝南居士
結語
今年的新年祝福語,大家喜歡說上一句“實‘鼠’不易,‘牛’轉乾坤”,將過去的“鼠”年以及迎來的“牛”年巧妙地點綴在成語之中,加上時事熱點的契合,使之瞬間在網絡上爆火。無論是傳說故事,還是與之相關地名,都能反映出人類與其他動物,千百年來微妙的關系,用一句網絡語言形容——“相愛相殺”。我們今天提倡的是“和諧共處”,正如西方一句名言“動物是另一種形態的人”,這顆藍色的星球,需要我們人類,也需要包括動物在內的所有生物!
 全攻略
全攻略

 全攻略
全攻略

 愛上合肥
愛上合肥

 肥肥集市
肥肥集市

 合肥房產
合肥房產